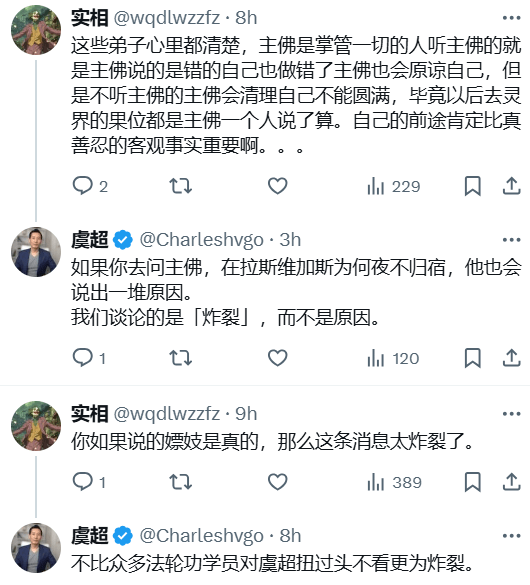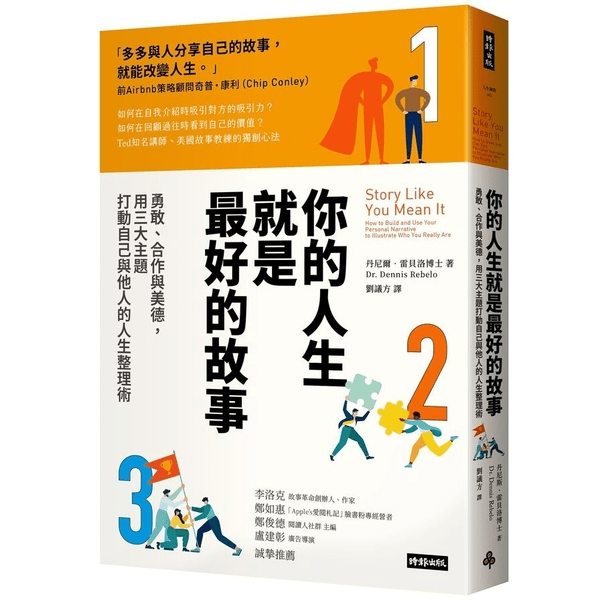今早我在臉書發文《看完虞超採訪我大哭一場》,也許是臉書「技術操作」的緣故,反應不大。但是在推特上,如油鍋入水,反應很大。一些面目不清的人立即罵我帶風向、大外宣。不過我熟悉的幾個法輪功弟子留言倒是非常溫和理性。所以,法輪功這個話題,中共比我們更起勁。因為法輪功一旦出問題,共匪就可以理直氣壯認為它們的鎮壓是合理的。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
我的文章出來以後,我第一時間發給了我在法輪功裡的幾個好友。期待聽聽他們的反饋。
我的一個好朋友非常在意,他不僅去看了虞超的採訪,還向一些當事人發文詢問。然後給我寫了一封長長的信。他整整一個上午都在為這件事忙碌,直到下午兩點才吃午餐。他的信也附錄了章天亮先生的對我的回覆。
我的法輪功好友來信全文:
我從頭到尾看完了虞超的採訪,沒有太多讓我「震驚」的地方,畢竟他之前也說過很多了。事實上,我曾經問過他,他自己見過的修煉後對法輪功有負面印象的人一共有多少,他說,十一、二個吧。我想,這些應該也包括他所接觸採訪過的「前神韻演員」吧。
前兩天我姪女帶著她先生和她女兒到我這裡玩了玩,住了一夜,她女兒是神韻樂團演奏竪琴的,現在結束演出季,有兩周假,所以我姪女和她先生從新西蘭過來,一家人在一起度假。
我們先假設虞超和他採訪的人說的事情部分全是真的,那麼那名「前神韻演員」有點像「原告」,虞超有點像檢察官或公訴人,那麼,如果我們要扮演道德法庭的法官或陪審員來對此事進行道德審判的話,我們應該先聽一聽「被告」方說什麼。只聽了一方說法就下結論,這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
據虞超說,他已經向美國執法部門舉報神韻的事情,並拿到了 case號,那麼相信美國執法部門已經介入。如果我們可以相信美國執法部門,那麼法律上的事實認定與最後的審判或處理結果,我想我們不妨等待一下美國執法部門的行為或宣判。我認為我們個人不具備強制性瞭解相關事實的權力、義務或條件。
從道德審判的角度,那位「前神韻演員」受到的最大的傷害(先假設她說的全是真的),就是一位姓高的老師踢她,打她。作為踢和打,動作的程度可以有很大的範圍,造成的實際傷害也可以有很大的範圍。當然另一種傷害是心理上的,這個全憑受害人的主觀感受而定。如果到了刑事傷害的程度,那麼讓我們期待美國執法部門可以做出認定和裁決。
其他的,我認為都是可以商榷,甚至是正常的。比如說,一般住校學生,學校也是封閉式管理的,家長自願把孩子送到那裡,你不能把這個說成是「人口販賣」。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管理規則,如幾點熄燈就必須睡覺,你也不能把這個叫做人身控制。按法律,家長有權決定把未成年人送到哪個學校去就讀。現在保守派人士對於美國的一些公立學校不經家長同意就給孩子做變性手術,不是也很反對嗎?所以,從原則上講,家長,而不是政府,才有權利決定自己未成年孩子的一些事情。現在甚至有些餐廳,你進去時都讓你把手機交出來,好專心吃飯。所以寄宿學校或藝術團不讓孩子用智慧手機,上網,我覺得很正常。
我記得我姪女送她女兒去神韻前就到處替她女兒買老人機,因為山上這樣要求的,而我姪女非常高興不讓她上網,因為上網的危害性,比起能從網上得到好東西的可能性更大。但是,請注意,孩子在山上仍然有電話,有手機,可以隨時與父母通話,也可以發電子郵件。
我姪女曾經帶著她兩個孩子在中城住過四年多,陪兩個孩子在飛天學校完成了中學學業。之後她女兒被神韻錄取,兒子回新西蘭上大學了,她也跟兒子一起回去,把在這裡買的房子賣掉了。從那以後,她女兒有什麼事她就托我幫忙辦。如去接她女兒下山配眼鏡之類。我接她女兒下山時,她女兒會用我手機上的軟件跟她媽媽視頻聊天,大家很開心,我沒看出任何她受到虐待的跡象。
她也跟我談到過山上怎樣學法修煉的事,都是修煉人之間的正常交流,沒有任何不對頭之處。
我姪女的兩個孩子,我從他們生下來時就認識他們,是看著他們長大的。我可以負責任地說,上飛天之前,他們是比較沒有禮貌的,每次我去她家,他們都不跟我打招呼的,根本不理我。現在的孩子就是這樣,沒辦法。上了飛天一年後,人就全變了,變得彬彬有禮,且知道為別人考慮,完全不一樣了。
神韻現在有8個團,每個團100人的話,我覺得整個恐怕有上千人了。所以,我想說,十幾個人的感受(其實我們現在只聽到一個人的親口講述),應該不能代表上千人的感受。我們要做出全面判斷的話,至少應該聽聽其他人的感受。當然,從法律角度上講,殺一個人的罪,也是大罪,也應該判刑。但是,法庭在定罪之前,會給被告說話的機會。當然,我並不是這件事的「被告」,也無法代表「被告」講話,只是從一個瞭解了一點別的情況的人的角度,跟你講講我所知道的。
還有就是,出國時護照統一保管。我想這也沒有什麼出格的。旅遊團有時護照還統一管理呢。演出團那麼多人,有的人年齡小,有可能是冒冒失失粗心大意之人。說不定上個廁所就把包忘在裡面了,如果因為一個人粗心大意把護照搞丟了,影響全團的行程,那這不是亂套了嗎?藝術團要保證演出日程,有些管理必須嚴格,不然不知道出多少差錯了。所以說,以平常心去看待神韻的話,很多事情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論。
還有就是利用孩子賺錢的說法。首先,孩子上去有沒有報酬,或報酬到底是多少,這之前家長是瞭解的,如果她們覺得沒問題,這就說不上剝削。就像我替新唐人大紀元做了十幾年的義工,我始終沒有覺得自己被誰剝削了,是我自願的。如果神韻的老師,或李洪志先生,拿著這些錢去花天酒地了,那確實就太可恨太罪惡了。但據我所知,沒有人這樣。神韻總部我去過多次,大家都是一起吃食堂,包括師父和他家人。有錢也沒地方花,每個人都忙得要死。神韻成立十幾年來,迅速的發展,和外出演出,買服裝道具,做廣告等各項費用都是驚人的,所以有收入都是投入在這些上了。
所以,凡是在裡面付出的,是為這個事業共同付出,如果是不自願的,那麼她可能覺得被剝削了;如果是自願的,她會很高興她所付出的事業,成長得很好了。但是,如果我換個角度看問題,我覺得我在媒體中付出了,現在卻是別人在當負責人,出頭露面都是那些人,他們成了名人了,而且能夠在媒體中做決定,甚至能夠把我開除了,那麼我心懷不憤,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也可能這樣去看:我曾經付出的事業成長了,成功了,我很高興,因為我本來就沒有想有所得。負責人的位置總得有人坐,不是張三,就是李四。在那個位置上,當然就有相應的責任與權力。這樣一想,我心就很平了。
對於神韻來說,複雜性在於,家長送孩子來的時候,可能都說這麼多錢,或不要錢是OK的,那神韻覺得家長是可以為孩子做主的,就這樣做了;但孩子長大後,覺得自己被剝削了,這就不太好辦了。但也有更多的孩子可能覺得沒被剝削,覺得能參與這樣的事業很光榮,很高興。所以,從道德層面,這事說不清楚。
但現在既然已經訴諸執法部門,就由執法部門來調查並認定吧。
虞超認定的神韻的另一個「罪行」是,神韻天天讓孩子們學法,法中講到有地獄,完不成使命不能圓滿甚至下地獄之類。他把這個稱為對孩子的恐嚇和脅迫。按這個說法,佛教和基督教也一直在恐嚇和脅迫教徒,因為經文和聖經中也講到做壞事要下地獄之類。
另外,您在法輪功學員家中住過,也看到他們天天做同樣的事。這也是恐嚇和脅迫嗎?不是的,這是他們在自由意志狀態下的選擇。
再說到邪教。不知在您心目中,邪教的標準和定義是什麼?如果以誰家的「理論」或教義來定義誰是邪教,按中共的標準,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邪教,包括基督教和佛教。如果以每個宗教自己的標準,大致其他宗教也都是邪教。不過,法輪功沒有說其他宗教是邪教。李洪志先生明確說過,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佛教、道教都是正教,他也贊成法輪功學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教會學校。
當然,他也說過,現在是末法時期,之前的宗教的神都不管人了,都離開了。沒有神管的宗教,就很難修,甚至修不成了。這不是他的原話,是我自己的理解。
中共迫害我們,最大的理由就是我們是邪教,警察也明確告訴我,我犯的是思想罪,把我們弄到勞教所唯一目的是轉化我們。在美國,是沒有邪教罪這一說的,也不會去定義誰是邪教。
個人犯罪,那是用法律來對待,也不會對團體下什麼定義。所以說,就算虞超採訪的人說的事全是真的,那也是那一個人有罪或有錯。當然您可以說可能還有更多的犯罪事實和受害者。但是,在我們瞭解到所有的事實之前,我們其實並不知道情況到底怎樣。
我想您知道這個事實:絕大多數的法輪功學員,根本不知道,也沒參與過神韻或山上的任何事情,特別是中國的學員。我也算是他們中的一分子。我們這麼多年做了些什麼,吃了多少苦,你是瞭解一些的。如果因為一個姓高的老師打了踢了一個學生,所有的這些與此事不相干的人都被戴上一頂「邪教徒」的帽子,您覺得對我們公平嗎?如果以行為定邪教的話,那我想至少得這個宗教中超過一半的人都是在乾違法犯罪之事,才能說是邪教嗎?天主教和基督教中,性侵兒童的不少,但沒有誰說天主教和基督教是邪教,為什麼對法輪功如此高的標準去要求呢?您想想這個場景:如果社會的輿論,都在說法輪功是邪教,那麼中共這麼多年的鎮壓,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了,那麼在美國,法輪功學員們都會有點抬不起頭來,也許神韻和大紀元新唐人也做不下去,慢慢倒台,法輪功這個團體,也就慢慢煙消雲散了。這是您願意看到的場景嗎?
您的帖子,是社會輿論的一部分。當然,如果您真心認為高老師的行為是修煉法輪功所導致的,法輪功的教義會導致人行惡,那麼您可以大聲呼籲,號召學員都別修了,或號召大家抵制法輪功。如果神韻藝術團就是一個折磨孩子、拐賣孩子的罪惡團體,那麼你也可以大聲呼籲,讓大家都來抵制。但是,如果高老師的行為不是法輪功教的,其他的法輪功學員沒有一個做惡的,甚至都是行善的多,那麼是不是不應該讓其他法輪功學員來背負高老師的罪孽呢(先假設它是成立的。)?
那個採訪中提到送包包的事情,我想請你看一下李先生的這篇文章 :《正確對待師父家人》你也知道,絕大部分法輪功學員,根本見不到李先生,或他的家人。他們修煉的唯一依據和辦法,就是反復閱讀李先生的書或文章。我在反復閱讀李先生的文章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感慨,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任何其他人這麼不厭其煩地教導他的弟子要做好人、做好人、做好人的。我真的非常感動。
還有就是,虞超現在顯然已經與王志安合作了,王採訪的對象,應該就是他介紹的。我能瞭解您的難過,因為您是善良的人,您看不得有人受苦,或世上有不公。但是,善心也有可能被利用,你想您瞭解這點吧?
我想我跟你說過,我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從幾年前就在臉書上推動虞超往前走的那個自稱法輪功學員的人,是個中共特務。以下是一位學者跟我私下交流時所說的話:目前的局勢太奇特,……一下冒出這麼多前法輪功學員,自認邪教不說,還逼著我這種局外人指控邪教。”我被動捲入,但我不是法輪功。而且我守住信仰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西方國家政府需要保護的公民權利這點,……不上他們的當——這波騷擾應該過去了。……我相信法輪功學員應該明白我的側面解圍(不是邪教)之意。”我覺得,這種立場是對的。
所以,從朋友的角度,我希望你不要輕易用邪教這個詞來形容法輪功。它的打擊和傷害面太大。我知道,您在心中對法輪功的看法和期許曾經是很高的,所以今天才會這麼受打擊。但是,我非常想請您先靜下心來,從各方面多想想。至於我,我倒覺得沒什麼太了不起的。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都走過來了,真的遵循真善忍的,在修煉中無所求的,都一定問心無愧。有沒做好的,如果是真修的,他會想改;如果個人做的錯事大到需要法律制裁,那麼法律也是只制裁個人,不會對與此事無關的人其他人怎樣。基督徒用了三百年才在世間立住腳。所以,法輪功未來怎樣,現在下結論可能太早。大家可以繼續觀察。
信件寫到這裡,我得到章天亮的回復了。我看完虞超的視頻後把鏈接發給了他,因為視頻最後提到他,說他對學生很好,他唯一的「罪行」是在台灣期間沒理那個前演員。他回應說:「 我對所有學生都很好。我後來跟她聯繫了,告訴她我時間太緊,連去夜市的時間都沒有。」過了幾小時,大約是他看了視頻後,他回應說:“我聽了一些她講的東西。我知道她是誰,也知道她說的大部分的事兒。但她說的她被打的事兒我不知道。
我問:有她所說的高老師這麼個人嗎?
他答:應該有,可能因為打學生被學校開除了。大陸的老師教舞蹈和體操都是那麼學出來的。說不上因為恨你折磨你而打你,而是你動作不到位,可能就會踢你相關的部位。
這個前演員,姑且叫她CC。疫情期間演出中斷,她已經畢業了,美國封關,她就回不來了,所以她就回了台灣。她因為回不來,就很失落。
我說:她說是山上不要她了。而且採訪中,她最難過的就是這點。他說:不是山上不要她了。當時美國封關了,誰也回不來。她中間自己想回山上,就自己飛到加州,然後美國就拒絕她入關。那時候她還跟我聯繫,大概可能想臨時找地方住。我就勸她找個工作,經濟上養活自己。她去找工作遇到了她現在的先生,也是搞舞蹈的,就嫁了。她還邀請我參加她的婚禮。台灣那麼遠,沒事兒也不可能專門跑一趟,我只能給她一些祝福,所以其實她畢業後不久就嫁人了。
CC下山之後,在台灣辦了舞蹈學校,覺得有的學生條件不錯,還找我,說要往山上送。那都是她離開一年多以後的事兒了她要是真的覺得山上不好,乾嘛要往山上送她的學生?就是這半年多,虞超影響了她先生。她先生又影響了她。她的臉書關掉了。原來頁面上有跟我照的畢業照,還說了很多感謝我的話。
我問他能不能把他說的這些告訴你,並說你因為看了虞超的視頻很難過,他說:可以啊,這是事實,沒啥不能說的。最後我建議他出視頻回應一下,他同意了。並說以前沒回應,是因為虞超說得很泛泛而談,“我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在說誰”,“現在有具體的人和事了,我作為當事人就知道了”。所以他說他應該會回應。